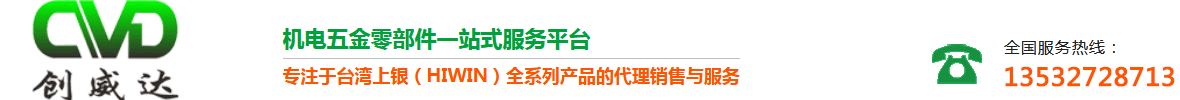经过40余年的改革开放,中国成功地实现了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的转轨,国家经济实力、科学技术实力、国防实力、综合国力得到前所未有的提升。
党的面貌、国家的面貌、人民的面貌、军队的面貌、中华民族的面貌发生了前所未有的变化。
在国际环境与一个国家的关系方面,不可能使国际环境的格局和变化去完全适应这一个国家,即使强国,也不可能根本性地改变国际环境来使其适应自己。这一个国家的行为要更多地适应国际环境的格局和变化;当然,一个国家根据其规模和国力,以及在国际上的地位,发挥主动性,可能会程度不同地影响自己所处的国际环境。
中华民族是世界上伟大的民族之一。在农业文明时代,1840年战争以前800年的时间内,中国的GDP一直占到世界财富总量的三分之一。在几千年的人类历史中,中国人在秦汉、唐宋、元明清等盛世时,创造了璀璨的中华文明。
到1765年,珍妮纺纱机的发明标志着第一次工业革命的开始,特别是蒸汽机的使用,世界进入工业文明,欧洲列国在世界崛起,西班牙和英国等,先后坐过世界领导国家的交椅。
1776年美国建国,自由的思想、创新活跃、比欧洲还要进步的资本主义制度、英国等产业向美国的转移、源源不断人力资源从欧洲的迁移以及大量廉价劳动力从非洲运来,使美国在大西洋彼岸迅速崛起。20世纪从英国手中夺得了资本主义的世界霸权,领导资本主义阵营与苏联社会主义阵营对垒。而苏联解体后,美国变成全球一超强大的国家。
如果说一个曾经创造过世界辉煌文明的强国,在17世纪开始衰败,那么在这漫长的200多年受侵略的历史中我们有着极其惨痛的教训,全球竞争中,先进的工业文明对落后的农业文明的胜利,开放的海洋经济对封闭的内陆经济的胜利,科学技术进步对因循守旧的胜利,也是近代国家政治体制对传统国家政治体制的胜利。
三十而立,四十不惑。新中国成立的前30年,技术进步对经济稳步的增长的贡献率走了弯路。建国后第一个10年为27.78%,中间10年是8.24%,而后10年只有4.12%。到1978年,人口为世界的25%,而GDP占世界总量比为1%,人均155美元,排世界倒数第二。
同期,欧美、日韩、中国台湾,技术进步对经济稳步的增长的贡献在50%到65%之间。在科学技术水平方面,中国在这30年时间里,形成了与这些国家和地区50年左右的差距。
实事求是地讲,除了成功发射氢核弹和卫星外,在经济强国的方面,从1840年衰败起,到1978年为止,我们仍就是一个落?后?的民族。
1978年开始的改革开放,才从建国梦的余辉中走出,真正开始了实现强国富民梦的征程。2022年,有14亿人口的中国,虽然GDP121万亿元,总量为世界第二位,仍然是一个发展中国家,人均GDP为85698元,约12741美元,连续两年保持在1.2万美元以上,为全球中等收入国家水平。
而2022年美国人均GDP为7.64万美元,日本人均GDP约3.49万美元,虽然日本仍是全球第三大经济体,但30年人均GDP没有增加,还低于1993年的人均GDP3.57万美元。然而中国远低于美国和日本的人均GDP。
凭着根植于中国梦的中国精神,追赶发达国家的人均GDP将成为可能。因为每一个中国人通过个人在创业和就业中的奋斗,实现自身安居乐业的需要以及所追求事业的成功。把未来与向往的城市命运捆绑在一起,“城里人”在城市里工作、居住和生活,成为新市民,并且城市改变我们的生活方式,实现自身美好的愿望。
到21世纪中叶时,把中国建设成一个人民富裕、国家强盛、社会安定、生态环境优美的社会主义强国,实现中华民族在21世纪的伟大复兴。
中国崛起的背后是自己独特的发展模式。我们大家可以用“儒家文明圈”或“筷子文化圈”来形容东亚的这些国家和地区。中国发展模式自然与“东亚模式”在很多方面一脉相承,也能说是“东亚模式”的一种独特的延伸。
所谓“东亚模式”主要指的是亚洲“四小龙”在相似的历史、文化背景下,采取了具有现代化导向的政府干预,实行赶超战略,尽管也存有不少问题,但这些社会大致实现了经济和社会的现代化。
2008年起源于美国的金融海啸又给了我们一个机会来重新审视“东亚模式”、“中国模式”及其相关的一些问题。与“四小龙”相比,中国也实现了现代化事业的起飞,同时还完成了由计划经济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深刻转变。
中国是一个14亿人口的世界性大国,所以中国崛起的模式自然具有“四小龙”不能够比拟的规模效应,对全世界的影响也将更为深广和久远。
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爆发后,美国和西方一些主流学者试图全面否定“东亚模式”,进而也否定“中国模式”。
具有讽刺意味的是,今天比亚洲金融危机严重无数倍的金融海啸竟起源于美国这么一个“民主典范”国家,而且美国这么“优越”的民主制度竟然对危机的爆发毫无察觉,对危机处理不当之处也比比皆是。尤其是近?期?美债达到了债?务?上限31.4万亿美元。
中国经济和政治体制改革的任务就是取百家之长,超越美国模式,发挥自己的优势,不断推动符合中国民情国情的制度创新。
在应对席卷世界的金融海啸中,中国展现了强大的宏观调控能力,使中国经济率先走出了金融危机的阴影,难怪美国金融家索罗斯多次感叹:中国是全球化的最大受益者,也是这场金融危机的最大受益者。
中国模式的这种政治文化逻辑使中国避免了一个又一个政治和经济陷阱,特别是避免了休克疗法、全盘私有化、金融危机、伪“民主化”导致的国家解体等重大陷阱,实现了中国今天的全面崛起。
中国今天具有世界上最强大的行政组织能力,这从举办奥运会、世博会、东盟会,应对金融海啸的过程中可见一斑。
中国大力推进民生的改善,特别在消除贫困方面,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绩。中国的一些传统智慧,如“摸着石头过河”、“欲速则不达”等,也被用来引导中国的渐进改革。
先是沿海开放,后来是沿江开放、沿边开放,然后是整个内地的开放,现在中国已形成了东西南北中全方位开放的格局,逐渐建立了21个自贸区。
中国现在的经济体制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这种经济体制本质上也是一种混合经济。它是“看不见的手”与“看得见的手”的混合,是市场的力量和政府的力量的混合,是“市场经济学”与“人本经济学”的混合。
中国人均耕地面积是世界上最低的国家之一,土地私有化带来的最大可能就是土地迅速向少数人集聚,造成广大农民失地而陷入贫困。
中国历史上的传统是“普天之下,莫非王土”,历代革命者的理想都是“耕者有其田”。中国现在没有效法西方的主流模式,而是把土地的所有权与使用权分开,把宏观整合与市场机制结合起来,结果形成了世界上最大的城市化进程、最大的房地产市场、最大的高速铁路网和世界第二大高速公路网,实现了高于发达国家的住房自有率,绝大多数农民的居住条件也大为改善。
随着“温饱”、“小康”目标实现,中国日益现代化,并和世界经济融为一体。在这样的一个过程中,我们已基本掌握了西方的“数目字管理”,有些方面比西方做得更好。与此同时,中国还发展了自己的“宏观整合力”。这种“宏观整合力”的基础包括了国家对土地、金融、大型骨干企业的控制权,包括了“集中力量办大事”的能力和宏观调控能力,也包括了大力推动民营经济实现跨越式的发展。
中央政府发挥着对这个超大型国家提供宏观指导和保证稳定平衡的作用,而各级地方政府通过税收、土地和政策等资源,吸引投资,推动了地方的就业收入和社会繁荣,最后促进了整个国家的迅速崛起,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都是推动中国经济发展的发动机。
中国不要削足适履去迎合西方经济学和政治学教科书上的教条,而是通过对中国模式的考察和研究来改写西方的教科书并撰写自己的教科书。
办好中国的事情,关键在党。“中国是一个大国,决不能在根本性问题上出现颠覆性错误,如果出现就没有办法挽回、没有办法弥补。”
党的十八大以来,就是处理好改革、发展、稳定三者之间的关系。改革是发展的动力,是实现长期稳定的基础;发展是改革的目的,是稳定最可靠的保证;稳定则是改革、发展的前提,也是发展的重要要求。
“一带一路”倡议提出快十年了,中国各地与世界有关国家积极开展“一带一路”建设实践,并取得了辉煌的成就。
2016年11月17日,联合国关于推进“一带一路”倡议内容的决议获得了193个会员国的一致赞同,其决议欢迎“一带一路”合作倡议,以共商、共建、共享为原则,以和平合作、开放包容、互学互鉴、互利共赢的丝绸之路精神为指引,以打造命运共同体和利益共同体为合作目标,呼吁国际社会为“一带一路”建设提供安全保障环境。
从地域特征看,“丝绸之路经济带”和“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呈现不同分布,且有部分交叉和会合,并会不断延伸下去。
2013年中国提出沿线世纪海上丝绸之路”倡议之后,似一块巨大陨石坠入海中,可谓“一石激起千层浪”,海中似乎风平浪静,难以观察到它的冲击力,只有站在海岸上才能观察到它“滞后”的巨大浪潮和影响力。
2013年,世界经济还处于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影响之中,有许多不确定性,世界经济平均增速仅为2.4%,发达国家的经济处在低迷阶段,失业率居高不下,居民消费不振,投资缺乏信心。各国政策出现了“以邻为壑”举措,世界贸易规则遭到滥用和破坏,国际自由贸易受到严重阻碍。
20世纪60年代以来,国际分工和产业出现了新趋势,在新的国际政治经济发展形势影响下,一些过去经济落后的国家和地区,经济得到迅速的发展,比如亚洲的中国香港地区、中国台湾地区、新加坡和韩国经济的腾飞,拉丁美洲的“经济奇迹”,中国、印度、巴西、俄罗斯和南非金砖国家迅速崛起,凸显了一批新兴经济体,使广大发展中国家看到了谋求经济发展的希望和路径。
中国作为发展中国家在经济发展道路的探索中取得了良好成绩,在40年的改革开放中取得了巨大成就,科学技术水平和生产能力得到非常明显提高。
但是,中国仍然不能摆脱发达国家先进科学技术和高端产业的控制,其发展空间受到严重限制,而且在国际经济治理规则方面受制于发达国家制度话语权。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世界银行(WB)、世界贸易组织(WTO)等都是由发达国家倡议和主导的国际治理机制。
亚太地区前几年出现的《跨太平洋战略经济伙伴协定》(TPP)极力拉拢越南、秘鲁等发展中国家,企图分化发展中国家,遏制中国发展和壮大。尽管美国特朗普政府声明退出TPP,但是日本接力主导的《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全面进展协定》(CPTPP)仍然逐步运行。可见,发达国家参与运行的国际组织活力比较强,有一定机制再生能力,而发展中国家有关的组织和机制呈现碎片化,有必要进行整合和治理。中国已申请加入CPTPP。
1997年东南亚金融危机发生后,中国保持人民币不贬值,并采取一系列的积极措施和政策,得到东南亚各国的认同和赞赏,显示了中国在国际经济治理中的作用与高度责任感,而且说明了发展中国家合作构建国际经济治理机制的重要意义。之后出现了以东盟为核心的中国—东盟、日本—东盟、韩国—东盟合作机制,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RCEP)经历八年谈判,去年生效,即东盟、中国、日本、韩国、澳大利亚、新西兰、印度共同参与的统一市场的自由贸易协定,开始构建发展中国家主导的国际经济治理机制。
在东盟及其范围更大的亚太经合组织(APEC)有关会议上,各国代表都认为亚洲各国基础设施落后,提出了加强基础设施建设的合作。
在中国与东盟主导下,APEC探讨的议题逐渐趋向于务实,各方合作愿望增强,积极落实APEC各种倡议。因此,APEC组织化程度有所提高,也影响到其他国际组织,推动亚太区域各类机制协调运行,促使各国抛弃“以邻为壑”的观念,并开始调整国内政策。发展中国家通过合作,积极支持WTO的有效运行,最终形成以WTO多边贸易体制为基础,各类双边机制和区域一体化为补充的国际经济治理机制。
中国经济增长新动力正在形成和培育之中,新增长点尚未形成,国内市场需求有待进一步开发,加上外部需求不振,经济运行走势分化,下行压力仍然较大,经济发展环境“硬约束”进一步加强。
“陆地丝绸之路”从中国西部出发,经过中亚5国,向南行到达南亚阿富汗、巴基斯坦、印度,向西行到达西亚的伊朗、土耳其,进入欧洲和中东地区,再向西南方向可以到达埃及及其他非洲国家。
“海上丝绸之路”从沿海各个港口出发,经过东南亚各国,穿过马六甲海峡,进入印度洋,到达南亚各国,沿海岸经过巴基斯坦和伊朗,到达波斯湾、红海湾和东非各国。
现代“丝绸之路”需要加强通道建设、港口相互连通建设。“海上丝绸之路”建设需要沿线国家建立良好的合作关系。
现代“海上丝绸之路”建设必须加强文化建设,发挥文化的非消极作用,其他建设才会走得更加顺畅、更加长远。“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建设是一个复杂的系统,“牵一发而动全身”。
“一带一路”建设的五大内容,即政策沟通、设施联通、贸易畅通、资金融通、民心相通“五通”,构成了“海上新丝路”建设的系统,缺一不可。
共建“海上新丝路”,是新形势下应对挑战、推动全球化继续深入发展的保障。不仅如此,包含“海上新丝路”在内的“一带一路”倡议构想已经引起了国内和相关国家、地区乃至全世界的高度关注和强烈共鸣,不仅对中国自身对外开放和经济发展产生重大影响,对国际社会也产生了巨大影响。